 《讀者》曾經為少年時代的我打開一扇通往詩意人生的窗戶
《讀者》曾經為少年時代的我打開一扇通往詩意人生的窗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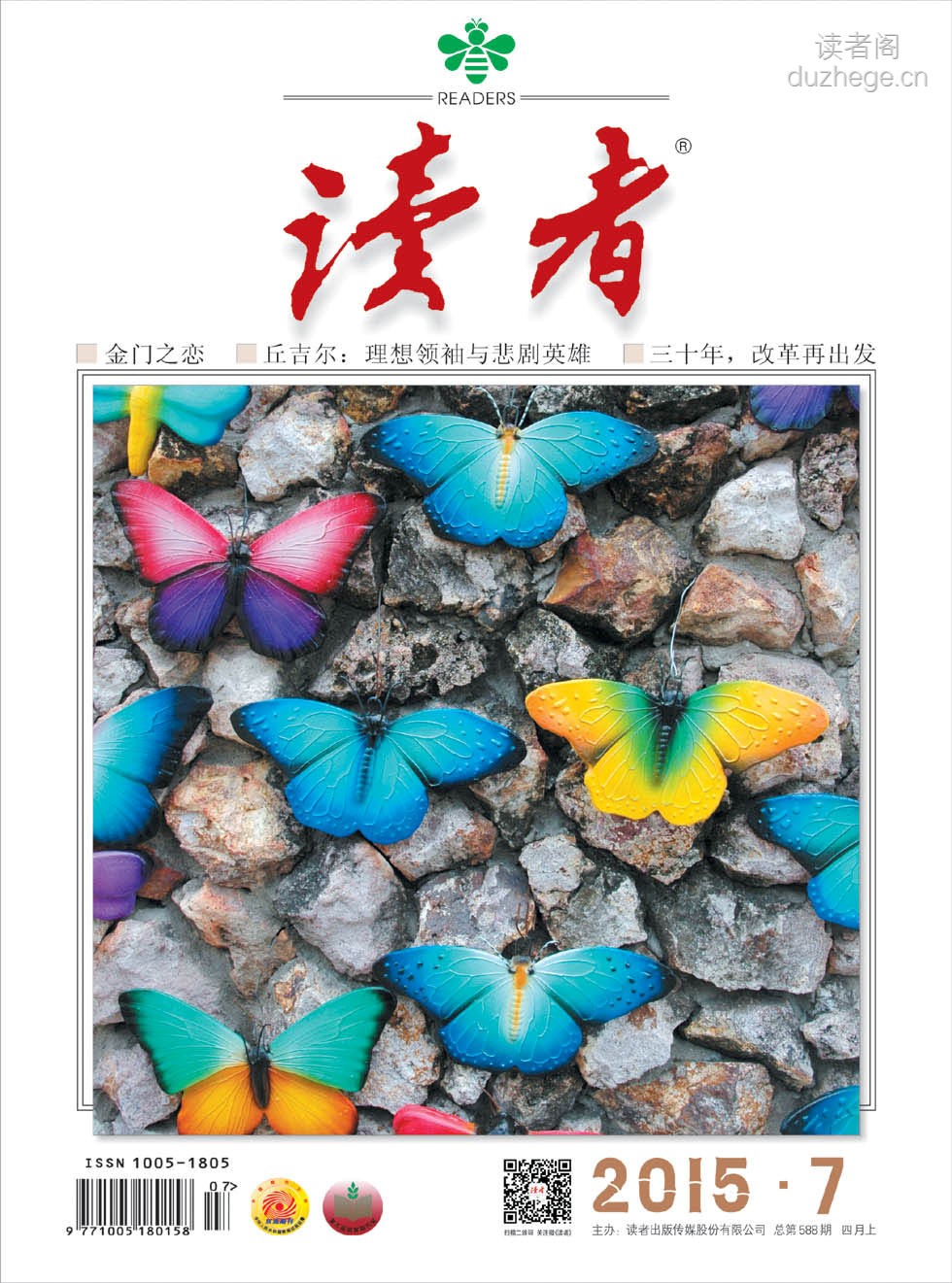
2021年夏日的一天,我帶兒子去費郡的一個社區圖書館,偶然發現雜誌架上唯一的一種中文雜誌是《讀者》。好像遇到一位老朋友,這本雜誌勾起我對青春時代的一段美好回憶。
在我讀中學時,《讀者》雜誌的名字還是《讀者文摘》——後來,為了避免與美國更早創刊、也更有名的《讀者文摘》同名,為尊重對方智慧產權的緣故,不得已改了名字。《讀者》雜誌的改名,可以看做是當時中國試圖與文明世界接軌的努力的一部分。
我最早知道有這樣一份雜誌,緣於我的一位愛好文學的姨媽。她沒有考上大學,卻在工作之餘唸了電大中文系。她常常給我講故事,故事很多都是從《讀者》上看來的。當我有了閱讀能力和閱讀慾望的時候,我從姨媽那裡借到這份雜誌,一翻開讀就不可抑制地愛上它了。
我是一個典型的韓寒所說的“小鎮青年”,在父母工作的一個濃煙滾滾的化肥廠廠區長大,童年時精神與物質同樣匱乏。幸虧有了一份《讀者》,我才眼界大開,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從這份雜誌上,十一、二歲的我第一次知道了狄更斯、羅曼·羅蘭、雨果、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等如同群星般閃耀的名字,一扇世界文學的窗戶緩緩打開。我通常是先讀到《讀者》雜誌上摘錄的片段,再去找原著來讀,如同找到金山銀山,一發不可收拾。我生長在川西平原的小縣城,卻在閱讀中神遊巴黎、倫敦和彼得堡,與大衛·科波菲爾和約翰·克里斯托夫們一起歡笑、一起哀哭。
《讀者》地處比我的家鄉更偏遠的甘肅蘭州,卻比北京上海的很多雜誌都更加“西化”,其發表的大部分稿件都來自於西方文學名著,就連封面設計都相當“非中國”。它一度成為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雜誌,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一九八零年代的《讀者》,一如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文化界,熱情洋溢地擁抱西方,擁抱自由、寬容、美和人道主義這些現代理念和生活方式。
多年以後,當我讀到作家王小波的一段話,尤其感謝《讀者》帶給我的文學藝術的啟蒙教育,我的審美品味多多少少是由《讀者》上刊登的西方文學大師的隻言片語所熏陶出來的。王小波說:「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讀者》上的很多短小精悍的散文,如同詩歌一般,我記得有一個名叫“意林”的欄目,是我最喜歡閱讀的,甚至還摘抄在筆記本上。我在寫高考命題作文時引用了“意林”中的一個段落,那個段落讓我的整篇文章增色不少,也使我的作文成為那一年四川省百萬考卷中屈指可數的幾份滿分作文卷之一。
《讀者》讓無數像我這樣文化生活貧乏的“小鎮青年”知道了什麼是好文章,什麼是好生活。正如王小波所說,好的文字,應該有詩性的光輝:「好詩描述過的事情各不相同,韻律也變化無常,但是都有一點相同的東西。它有一種水晶般的光輝,好像來自星星……真希望能永遠讀下去,打破這個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寫這樣的詩。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顆星星。」多年以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了一顆星星,卻如願以償地選擇了文字生涯。我從《讀者》雜誌的讀者,變成了作者之一。很多讀者將我的散文推薦給《讀者》發表,我時常收到它匯來的比其他媒體高得多的轉載稿費。
因為有一份溫暖的回憶,我從圖書館中將2021年第七期的《讀者》雜誌借閱回家。然而,當我打開這份久違的雜誌,才發現它已然面目全非,它的字裡行間充斥著一種習近平式的蠻橫粗暴的僵屍氣味,就好像在停屍房中待久了,身上不知不覺染上死亡的氣味一樣。
一夜之間,《讀者》從擁抱文明到向野蠻下跪
《讀者》封面的風格數十年不變,優雅柔美,大都是取自西方攝影名作,但其內容卻今非昔比。它不再是西方的學習者和西方文化的傳播者,而是西方的敵人和西方文化的踐踏者。在這期雜誌中,西方作者的作品分量大大降低,中國作者的作品尤其是直接從網絡上摘錄的比例大大提升。那些網絡上的文字,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粗鄙卑賤的風格,這就是所謂的“接地氣”嗎?
粗鄙卑賤還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那些文革式的、殺氣騰騰的文字施施然地登堂入室。《讀者》幾十年來一點一滴地養成的尊重和敬畏文明的特質,在一夜之間幾乎蕩然無存。毛澤東式的痞子文風佔了上風,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將「痞子」譽為革命最積極最堅決的人,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員。毛澤東意識到,只有靠痞子才可以「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習近平就是毛澤東的痞子文化的傳承人,他扭轉了中國走向文明開化的方向,重新將中國拉入閉關鎖國的泥沼之中。面對這一新的時代環境,《讀者》改換門庭,投其所好,大力配合,如此才有在這個超納粹帝國的存身之地。
在這一期的“言論”專欄,首當其衝的兩則言論是——“清澈的愛,只為中國!”這是十八歲的戍邊英雄陳祥榕入伍時寫下的戰鬥口號,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我們就是祖國的界碑,腳下的每一吋土地,都是祖國的領土。”這是肖思遠的戰地日記,這也是英雄戰士們的戰地誓言。編輯只差沒有用粗體字或紅色字體來顯示英雄的宣告了。然而,士兵的愛國其實是無用功:難道不正是習近平在普京面前卑躬屈膝、承認俄國“合法”佔據中國大片土地嗎?這兩位英雄是不是應該立即處決作為賣國賊的習近平呢?
同一期雜誌上,還有一篇題為《一個國家的英雄基因就這樣生生不息》的文章,歌頌在中印邊境衝突中喪生的軍人,“驕傲於他們以一敵十、不辱使命,憤怒於個別敗類侮辱祖國的英雄”。然而,這些軍人算不上英雄,只是獨裁政權的炮灰而已——那些維權的越戰老兵的淒慘命運,有誰關心呢?有哪家媒體敢報道呢?這篇文章搬出毛時代的左派作家魏巍的那篇用謊言編織成的文章《誰是最可愛的人》——這篇所謂的報道文學,是中共偽造的韓戰歷史中一塊不能被質疑的神主牌。當年,我撰文指出該文章的若干錯誤,立即招致中宣部鋪天蓋地的大批判。
同一期的雜誌中,還刊登了一篇新華社的長篇報道《芳華無悔》,用央視播音員的煽情口吻描寫離開大城市到廣西百色一個村子當黨支書的北師大畢業生黃文秀的故事,所謂“用生命踐行了一名共產黨員對信仰的無比忠誠”。這種造神文宣是毛時代秀才們的拿手好戲,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是焦裕祿。國際歌宣稱世上沒有救世主,中共的宣傳機構卻將其領袖及各式各樣的共產黨員塑造成中國的救星。這種文章出現在新華社、《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上不足為奇,出現在《讀者》上則讓人扼腕長歎。
《讀者》背離了過去數十年來的傳統和初衷。文明被野蠻所吞噬,這樣的悲劇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上演。當《讀者》變成了喉舌、變成了戰狼、變成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吹鼓手,“中國離文革還有多遠”這個問題也就有了答案:中國離文革僅有咫尺之遙。
(本文僅代表作者意見,若有任何指教,歡迎來稿)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